呼兰河传
民国著名作家萧红代表作品,在《亚洲周刊》组织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作品中,《呼兰河传》排名第九,堪称影响数代人的经典。
作者:萧红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时间:2017-12-01
开本:16开页数:256
定价: ¥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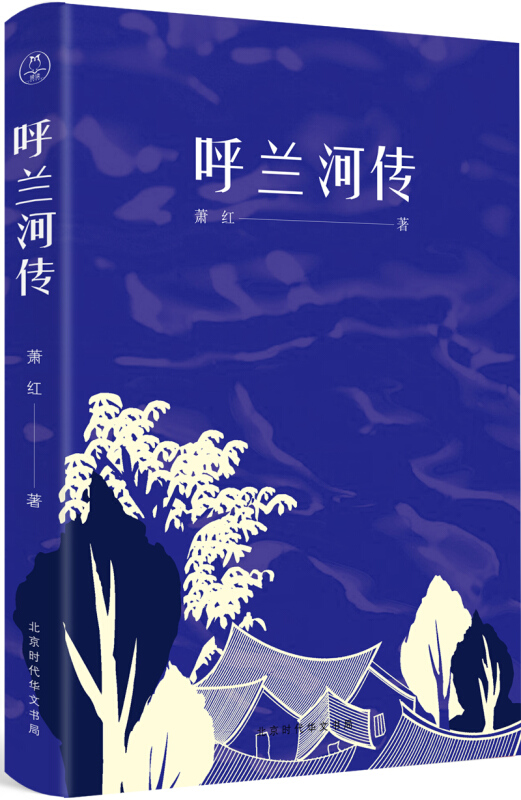
呼兰河传 版权:
ISBN:9787569919110
条形码:9787569919110 ; 978-7-5699-1911-0
装帧:简裝本
版次:1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印刷次数:1
所属分类:小说>世界名著>亚洲
呼兰河传 特点:
(1) “文学洛神”、民国著名作家萧红代表作品,在《亚洲周刊》组织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作品中,《呼兰河传》排名第九,影响数代人的经典。
(2)忠实复原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首次出版版本。
(3)萧红32年短暂生涯的一部“回忆式”长篇小说,是研究她早期生活的重要资料。
(4)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以女性的目光洞悉历史的真实,达到对现代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彻悟
(5)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座萧红笔下的“后花园”,那里有故乡、亲人、往事,有让一个人走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1) “Luoshen of literatur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Xiao Hong, a famous writ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nk ninth among the “top 100 Chinese 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selected by Asia Weekly, which has influenced generations.
(2) Faithful restoratio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Guilin Heshan publishing house in 1941.
(3) Xiao Hong’s “reminiscent” novel, a short career of 32 years,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her early life.
(4) By recalling all kinds of characters and life pictures in his hometown,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negat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 of distorted human nature and damaged personality in old China. Women’s insight into the truth of history, to achie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oul
(5) Everyone should have a “back garden” in Xiao Hong’s works, where there are hometown, relatives, past events, courage and strength to let a person go.
呼兰河传 简介:
《呼兰河传》是萧红*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在《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调描写了以家乡为原型的“呼兰河城”的传记。全书共分,七章,它以作者的童年回忆为引线,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东北小城呼兰的种种人和事,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地老百姓平凡、卑琐、落后的生活现状和得过且过、平庸、愚昧的精神状态。但萧红还是用淡泊的语气和包容的心叙说了家乡的种种。她将一片片记忆的碎片摆出来,回味那份独属于童年、独属于乡土的气息。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Xiao Hong. This work is ranked ninth among the top 100 Chinese 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the “Asian Literary World” in Hong Kong. In the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City in prose style.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It depicts all kinds of people and things in Hulan, a small northeast city in 1920s, based on the author’s childhood memories. It truly and vividly reproduces the local people’s ordinary, trivial and backward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spirit of muddling along, mediocrity and ignorance. But Xiao Hong still narrates all kinds of things in her hometown with her indifferent tone and tolerant heart. She put out pieces of memory and savored the flavor of childhood and countryside.
呼兰河传 目录:
目录
**章 / 001
第二章 / 051
第三章 / 085
第四章 / 129
第五章 / 157
第六章 / 219
第七章 / 259
尾声 / 299
呼兰河传 摘选: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店,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使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检萧红的文章中,有部分字词反映了当时或自己的用字习惯,与现在常用字不同。本书保留这部分异形字词的原有写法,尽量恢复初刊原貌。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了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二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个叫做东二道街,一个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火磨:用电动机或内燃机带动的磨。此处代指面粉加工厂。,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的高,农业学生开头是念“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账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到:“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有?”小秃子就是他的八岁的长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因为他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没有?大豆卖了没有?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万里干坤的“亁”和干菜干菜:蔬菜的干制品。的“干”,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干菜的“干”应该这样写:“亁”,而不是那样写:“干”。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便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份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潋糊,比浆糊还粘。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而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旱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也要没顶的。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可是若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的干下去,到后来也不过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试探着冒险地赶着车从上边过去了,还有些次勇敢者,看着别人过去,也就跟着过去了,一来二去的,这坑子的两岸,就压成车轮经过的车辙了。那再后来者,一看,前边已经有人走在先了,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赶着车子走上去了。
谁知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过去了,可是他却翻了车了。
车夫从泥坑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而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之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
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的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就这样的马要站起来,而又站不起来的闹了一阵之后,仍是没有站起来,仍是照原样可怜地躺在那里。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于是星散开去,各自回家去了。
现在再来说那马还是在那里躺着,那些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的担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他们卷卷裤脚,脱了鞋子,看看没有什么办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几个人的力量把那马抬起来。
结果抬不起来了,那马的呼吸不大多了。于是人们着了慌,赶快解了马套。从车子上把马解下来,以为这回那马毫无担负的就可以站起来了。
不料那马还是站不起来。马的脑袋露在泥浆的外边,两个耳朵哆嗦着,眼睛闭着,鼻子往外喷着秃秃的气。
看了这样可怜的景象,附近的人们跑回家去,取了绳索,拿了绞锥。用绳子把马捆了起来,用绞锥从下边掘着。人们喊着号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桥梁似的,把马抬出来了。
马是没有死,躺在道旁。人们给马浇了一些水,还给马洗了一个脸。
看热闹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说: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
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觉得那大泥坑也太没有什么威严了。
在这大泥坑上翻车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冬天冻住的季节之外,其余的时间,这大泥坑子像它被赋给生命了似的,它是活的。水涨了,水落了,过些日子大了,过些日子又小了。大家对它都起着无限的关切。
水大的时候,不但阻碍了车马,且也阻碍了行人。老头走在泥坑子的沿上,两条腿打颤,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的涨得溜溜的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的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的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
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是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那都不说。再说那后来的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弄了五六分钟之后,又过去了。
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来的人,向那正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着的人说:
“这算什么,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那不算英雄。”
可也不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饱满的,而大半是被吓得脸色发白。有的虽然已经过去了,还是不能够很快的抬起腿来走路,因为那腿还在打颤。
这一类胆小的人,虽然是险路已经过去了,但是心里边无由的生起来一种感伤的情绪,心里颤抖抖的,好像被这大泥坑子所感动了似的,总要回过头来望了一望,打量一会,似乎要有些话说。终于也没有说什么,还是走了。
有一天,下大雨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掉下去,让一个卖豆腐的救了上来。
救上来一看,那孩子是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
于是议论纷纷了,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学堂设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了,龙王爷要降大雨淹死这孩子。
有的说不然,完全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在讲堂上指手画脚的讲,讲给学生们说,说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龙王爷下的雨,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的气死,他这口气那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有的说,那学堂里的学生也太不像样了,有的爬上了老龙王的头顶,给老龙王去戴了一个草帽。这是什么年头,一个毛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老龙王怎么会不报应呢?看着吧,这还不能算了事,你想龙王爷并不是白人白人:平民百姓。呵!你若惹了他,他可能够饶了你?那不像对付一个拉车的,卖菜的,随便的踢他们一脚就让他们去。那是龙王爷呀!龙王爷还是惹得的吗?
有的说,那学堂的学生都太不像样了,他说他亲眼看见过,学生们拿了蚕放在大殿上老龙王的手上。你想老龙王那能够受得了。
有的说,现在的学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万上不得学堂的。一上了学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
有的说他要到学堂把他的儿子领回来,不让他念书了。
有的说孩子在学堂里念书,是越念越坏,比方吓掉了魂,他娘给他叫魂的时候,你听他说什么?他说这叫迷信。你说再念下去那还了得吗?
说来说去,越说越远了。
过了几天,大泥坑子又落下去了,泥坑两岸的行人通行无阻。
再过些日子不下雨,泥坑子就又有点像要干了。这时候,又有车马开始在上面走,又有车子翻在上面,又有马倒在泥中打滚,又是绳索棍棒之类的,往外抬马,被抬出去的赶着车子走了。后来的,陷进去,再抬。
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
有一次一个老绅士在泥坑涨水时掉在里边了。一爬出来,他就说:
“这街道太窄了,去了这水泡子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两边的院子,怎么不把院墙拆了让出一块来?”
他正说着,板墙里边,就是那院中的老太太搭了言。她说院墙是拆不得的,她说好种树,若是沿着墙根种上一排树,下起雨来人就可以攀着树过去了。
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
原因是这泥坑上边结了一层硬壳,动物们不认识那硬壳下面就是陷阱,等晓得了可也就晚了。它们跑着或是飞着,等往那硬壳上一落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白天还好,或者有人又要来施救。夜晚可就没有办法了。它们自己挣扎,挣扎到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沉下去了,其实也或者越挣扎越沉下去的快。有时至死也还不沉下去的事也有。若是那泥浆的密度过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
比方肉上市。忽然卖便宜猪肉了,于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来了,说:
“可不是那泥坑子里边又淹死了猪了?”
说着若是腿快的,就赶快跑到邻人的家去,告诉邻居:
“快去买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会没有了。”
等买回家来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肉。
但是又一想,那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
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是瘟猪肉。
可是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那么还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口猪,或两三口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至于居民们常吃淹死的猪肉,这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龙王爷晓得。
虽然吃的自己说是泥坑子淹死的猪肉,但也有吃病了的,那吃病了的就大发议论说:
“就是淹死的猪肉也不应该抬到市上去卖,死猪肉终究是不新鲜的,税局子是干什么的,让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卖起死猪肉来?”
那也是吃了死猪肉的,但是尚且没有病的人说:
“话可也不能是那么说,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的吃下去还会好。你看我们也一样的吃了,可怎么没病?”
间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时务,他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瘟猪肉。
这样的孩子,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用眼睛瞪着他,说他:
“瞎说,瞎说!”
有一次一个孩子说那猪肉一定是瘟猪肉,并且是当着母亲的面向邻人说的。
那邻人听了倒并没有坚决的表示什么,可是他的母亲的脸立刻就红了。伸出手去就打了那孩子。
那孩子很固执,仍是说:
“是瘟猪肉吗!是瘟猪肉吗!”
母亲实在难为情起来,就拾起门旁的烧火的叉子,向着那孩子的肩膀就打了过去。
于是孩子一边哭着一边跑回家里去了。
一进门,炕沿上坐着外祖母,那孩子一边哭着一边扑到外祖母的怀里说:
“姥姥,你吃的不是瘟猪肉吗?我妈打我。”
外祖母对这打得可怜的孩子本想安慰一番,但是一抬头看见了同院的老李家的奶妈站在门口往里看。
于是外祖母就掀起孩子后衣襟来,用力的在孩子的屁股上啌啌的打起来,嘴里还说着:
“谁让你这么一点你就胡说八道!”
一直打到李家的奶妈抱着孩子走了才算完事。
那孩子哭得一塌糊涂,什么“瘟猪肉”不“瘟猪肉”的,哭得也说不清了。
总共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
**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呼兰河传 作者: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Xiao Hong (1911-1942), a woman writer in modern China, is one of the four talented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1, he was born into a feudal landlord family in Hulan District, Harbin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1932, I met Xiao Jun. In 1933, he published his first novel, abandoned child, under the pseudonym of whispering. In 1935, with the support of Lu Xun, he published his famous work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In 1936, he went to Japan and wrote prose “lonely life” and long poem series “sand”. In 1940, he arrived in Hong Kong with Duanmu Hongliang, and later published the novella Ma bole and the novel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On January 22, 1942, he died of tuberculosis and malignant tracheectasis in Hong Kong. He was only 31 years old.
*书籍信息收集于网络,仅供参考,请支持正版!!!